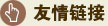山情
作者:于新生 时间:2006-08-28 点击:5118

在沂蒙山写生
山情
于新生
山,算不上奇;水,算不上秀。村,不富裕;人,不漂亮。可你不能说这里不美!
山养活了这里的人;人装扮了这里的山。这里,山和人完全地揉在了一起:揉得那样执“迷”不悟,揉得那样完全彻底。
沂蒙山,沂蒙人。
你质朴、纯真、刚正、善良。你让我念念不忘! 你让我久久痴迷!
“要饭的?”
红叶漫过了山头,火烧一样地红。
这一大片热情漾溢的美,惹得我这山外人好一阵子地激动。可留意那些山里人,对此却是一副习以为常地无动于衷。问及那些红树的名字,说:“不知道书本儿上叫什么,此地儿叫它黄栌柴,这树既不结果儿,又不成材儿,只能烧火做饭。”再问:“这么好看的东西怎舍得当柴烧?”答:“这满山都是,有啥好看?!”
嗬! 美,在这里竟是如此地奢侈!
山村的房舍依山傍水,随势而筑,穿插错落,扑朔迷离。院落里,收成的玉米、高粱、地瓜、山楂、柿子挂在树上、墙上,摊在地上、房上,它们明亮的色彩在灰土色的院落里闪耀。房舍内,没有任何不实用的装饰,没有任何虚荣的摆设,锅、碗、瓢、盆、坑、橱、箱、柜随遇而安,少了僵硬刻板,多了生动自然。这里,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那样的协调! 那样的平和!那样的自然而然!
顺着曲曲拐拐的石阶小巷,我不自觉地在山村中串了起来。登至山村高处,一位正在切山楂片的上年岁大娘望着走进她家门的我,问:“干啥来?”我忙答:“大娘,我来你这儿拍几张照片。”“什么?收山楂片儿?”我一听,知道大娘的耳朵有点背,于是拍拍身上的背包,放高声说:“大娘,我是来这画画的!”“什么?要饭的?”大娘这一问,着实地让我吃了一大惊。可是再看看自己这副德性,与要饭的又有什么不同呢?
是“要饭的”! 我正是到这里来:要真!要善!要美!
大嫂
路崖下的房舍在秋色中时隐时现,每家那平平的房顶都是一个收获的场院;每个收获的场院又都是一幅多彩的画面。
突然,我眼前一亮,脚步停了下来。
这儿,太美了!美得简直有点儿“胡闹”!几个房顶场院高低相宜、错落有致地挨在了一起。柿子被一串儿一串儿地挂了起来,连成了黄黄的好几大片,就像座座金色的城楼。玉米被编成辫儿整齐地叠压堆积着,就像个个金色的宝塔。白白的是瓜干,红红的是山楂。一个带绿头巾的大嫂正在房顶上忙碌,更使这山村美景增添了一番迷人的风情和人意……
“大嫂,忙呢?你这里太好看了,什么都有!”我上前打着招呼。
“什么都有?可就是没有钱!”
我的心被突然触动了一下,竟一时无言以对……是啊!这里缺少的不是美景,而是富有!但是:那城里人虽然阔气,可阔气的氛围里却多了污染;这山里人虽然土气,可土气的环境里却充满了纯净。
当我要给大嫂画张画时,大嫂便不自然了起来:“画啥来! 从早上到现在脸都没洗,这袜子都没穿,画到画上还不丑死?你们城里那么多的大美人儿,来这山沟里画我这丑婆子干啥?”我说:“那大美人儿让我画,我还不画哩!我就想画你这朴朴实实的山里人。”大嫂没再拒绝,可仍然是一脸不情愿地别扭。
我突然觉得:山里人也是那样的爱美,这是一种不靠外表打扮的美,一种内在的美。
汉子
村边,一个正在帮人盖房的汉子吸引了我,他那张长长的棱角分明的脸,显现着岩石般地坚强和刚毅。好一个典型的山里汉子!
我凑上前去试探着问:“大哥,能不能配合一下,拍张照片?”
“不拍!”那汉子直截了当。
“拍张照片怕什么,又不会担误你多长时间。”我不愿放弃地说。
“不拍!”汉子还是那句话。
没办法,只好离开。
可不知咋的?这汉子越是不让拍,就对我越有吸引力。我转了一大转后,又回到了那里。这次我决定来个突然袭击,既成事实看你咋办!可没想到那汉子早有准备,当我突然端起相机时,他便狠狠地把脸转向了一边,我拍到的只是他的后脑勺儿。
我只好又走过去恳求道:“我是画画的,想把你画到画里去。”
“你画画跟我啥相干,不拍!不拍!“汉子手里挥动着盖房的砖头。
就在这时我举起了相机……
汉子则向我举起了砖头……
我按下了快门……
汉子把砖头向我虚晃了一下,然后狠狠地砸在了地上……
好烈性的汉子!
我喜欢这汉子刚正倔强的烈性,相信他如果在战争年代肯定是个英雄。我真希望他能理解:我的“冒犯”完全是善意的,我是真心地希望跟山里人做朋友。
大爷
一位坐在山村石阶上的大爷老远就向我们打起了招呼。
当得知我的几位同伴是从北京来的时,便问道:“既然是从北京来的,那我得考考你。你说说:北京到底有多少门?”
这一问倒把几个同伴给问住了,竟无人能答。
大爷得意起来:“这你们可住瞎了北京了。”接着说快书似地背了起来:“有:天安门、地安门、东安门、西安门、东直门、朝阳门、西直门、阜成门……共二十四门。”
嗬!这老大爷可真是不简单。
旁边儿的人说:“大爷是去过北京见过世面的人,外面的事儿知道得可多啦。”
我说:“外面的事儿我们现在不想知道,倒是非常想听听这山里的事儿。”
“这山里的事儿有啥说头儿?山上种上粮食、果树,靠天吃饭,好天好收,歹天歹收。再就是垒墙盖屋,生儿育女,年年如此!”
山里的事儿在大爷的眼里竟是如此地“简单”! 可我知道这完全是一种对家园熟视无睹而又撕扯不断的依恋。我望着大爷那张布满皱纹、艰辛而苦涩的脸,这里边涵盖着多少勤劳和坚韧、苦痛和灾难、依恋和悲欢、想往和祈盼……
此刻,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:到过一天的地方可以说上一辈子,住过一辈子的地方一天也说不上。这“没啥说头儿”的沂蒙山,也许我要说上你一辈子。
大娘
与同伴们在一道矮墙上坐了下来。对面是一座低矮的石屋,石屋前有一道石墙夹着一个不大的柴门儿围成了一个小小的院落。
柴门儿响了一下,一位面目慈祥的大娘向外探出了半个身子。当看到我们手中拿着相机时,又很快地缩了回去。过了一会儿,院子里传出了大娘的声音:“我想跟你们说会话儿,可你们千万不兴给我照相!”我不明白大娘为啥这么害怕照相,但我们尊重大娘的意见。
大娘走了出来,手里托着几个熟透的柿子。
大娘的柿子真甜!
大娘说:“这是儿子送来的,看着你们吃,我心里舒坦。今年柿子收得少,贵得很,儿子只拿了几个过来。去年收得多,送来了一大提篮儿,我全拿给来这画画儿的学生们吃了。”原来,大娘仅有的几个柿子全给了我们。
问及大娘的生活,大娘说:“今年八十五了,身板儿还好,现在自己过。有儿子,有女儿,只是我现在上了年岁儿,帮不了他们什么。他们现在都过得不错,只要儿女过得好,我心里就高兴。”
多么善良慈爱的老人!我真想为老人做点什么,于是掏出了一点儿带在身上不多的钱,对老人说:“大娘,作为晚辈我想孝敬孝敬您,这点儿钱请您收下。”
大娘急了,死活不要:“你们看不起大娘了,我现在过得很好,吃得有鱼有肉,什么都不缺。”
真是这样?我走进了大娘的房子,光线幽暗的石屋里,仅有一套破旧的铺盖和简单的炊具,根本没有什么鱼肉的影子。好一个宁愿自己清苦,也不愿麻烦别人的大娘,这也许就是山里母亲们最为真实地写照:她们清苦,却从不说自己苦,或者说她们从来就不认为自己苦,因为这苦对她们来说,早就是习以为常的了。
我把钱硬塞到大娘手里,转身就走,可大娘紧追几步,硬是把钱向我扔了过来。我望着大娘那慈爱的脸,觉得:金钱在这位沂蒙山母亲面前,真地算不上什么了。
走远了,我回过头去,大娘依然在矮墙边望着我们。
我心中一热,挥手高喊:“大娘! 我还会来看您的!”
就要离开沂蒙山了。小酒店里,我端起了酒杯向伙伴们提议:“来! 让我们为了沂蒙山!”大伙儿一饮而尽。我觉得鼻子有点儿发酸……
我知道,我已深深地爱上了你:沂蒙山。
2001年9月于沂蒙山

切山楂片的大娘 (2001) 于新生

汉子 (2001) 于新生

中年男子 (2001) 于新生

中年男子 (2001) 于新生

拿拐杖的老人 (2001)于新生

大娘(2001) 于新生